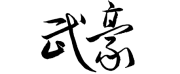唯美、诗意与浪漫幻想
——魏小明雕塑作品漫谈
Aestheticism,Poetry and Romantic Fantasy
—— On Wei Xiaoming’s Sculpture Works
武豪
摘要
雕塑家魏小明上世纪80年代以连环画作品《黑骏马》为国内艺术界所熟知,其后他从维也纳美术学院留学归国并逐渐转向雕塑创作,形成了独特的个人艺术风格。魏小明以人体雕塑为主的创作,表现出唯美、诗意和浪漫幻想的显著艺术特征,但唯美浪漫显然只是其作品的外在表象,唯有深刻认识到美背后“人”的维度及源自中国文化脉络中的浪漫传统,才能真正理解其作品在当下的价值所在。
关键词:唯美;诗意;浪漫幻想;魏小明雕塑
在中国雕塑家群体中,魏小明是一个独特的现象。这种独特性不仅是他艺术生涯中由平面设计转向版画创作又转向雕塑的多变,更重要的是他在许多中国艺术家不断追赶西方艺术潮流的善变路线中,对“美”和“人体雕塑”的执着和坚守,因为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在“美已成为过剩资源”[]和人体早已不再是艺术家和观众关注的对象的当下,魏小明的背道而驰,显然是一种“冒险”——他坚信美和情感可以穿越时代,不受潮流的左右。如果唯美、浪漫是魏小明雕塑最为显著的标签,那么循着由“美”带来的线索,那些隐蔽其中的价值或许更值得我们好奇和探究。
一、对美的迷恋与身体赞歌
把美提升为雕塑创作的第一需求,是魏小明雕塑的首要特征。他以一种极致化的视觉语言,把理想的人体美提升到了纯粹化的高度,这种纯粹化即:为了“美”的呈现,弱化了写实人体雕塑中客观形体、理性再现的羁绊和干扰,以一种近乎抽象化的造型方式,让韵律、节奏、线条、比例、和谐等形式美感得以最大程度的显现。
在这些“美”的人体雕塑中,一类是纤细柔美,或静谧如眠、或激扬欲飞的女人体雕塑。在这些作品中美是作为第一表现要素的,形体、线条、姿态、韵律等都要服从美的需要,甚至人物肢体伸展的角度,肌肉拉伸变化的形状,也要以展现美为第一原则。极致的形式美感,让这些人体雕塑带有少许矫饰的同时,也把它们同那些世俗的、生活化的、展现肉欲与性感的女人体雕塑区分开来——那些恣意扭转着的姿态,呈现出一种没有言说、没有目的、不被观看的自得状态,它(她)们自我游戏着,洋溢着生命的喜悦。如果说蕴含着力量的男人体雕塑大多来自艺术家自我的投射,那么这些充满生命愉悦感的女人体雕塑,则是理想的幻化,生命的赞歌。美只是一种表象,一个通道,一座桥梁,透过人体之美,艺术家追求与表现的正是人性中的至真至美,一个鲜活自足的生命,一段诗意的人生体验。
在近些年的女人体雕塑创作中,魏小明在材料上越来越多的使用汉白玉来雕刻。汉白玉的使用更加深了他人体作品中对单纯、静穆、纯净之美的呈现。材料本身的纯洁无瑕、温润剔透,使那些舒展着腰肢的青春少女,展现出一种冰清玉洁的纯洁意味。凝视这些洁白的汉白玉人体雕塑,它们总会给我们一种生命如此美好的慰藉和愉悦,无需哲理和知识,我们就能在这些美的感召下,体验生命中那些易逝的纯净、青春与美好。
在魏小明另一类雄健的男人体雕塑中,美的特征表现出显著的力量感——强大、雄浑,但并不霸悍张扬,相反,这种沉静的力量往往还隐藏着一种命运的悲剧性,这与他塑造的轻快飞扬的女人体,形成一种戏剧性的反差——轻与重、清与浊、喜与悲,交错缠绵,若即若离。雕塑《河床》是创作于2000年的作品,在这件作品中,魏小明塑造的两种美清晰的展现在相拥的两个男女人体之上:男人体交错隆起的肌肉覆盖在粗壮的肢体之上,像沟壑连绵的山地,透射出生命的厚度和时间的沧桑;与之相对的是相拥的女孩,姿态舒展,肢体纤长圆润,犹如一瀑清泉,在山壑间缓缓流动,雕塑中形体的繁简和节奏的急缓巧妙的在两个人体上展现出来,达到一种和谐和平衡。在塑造符合美的规律的人体中,我们完全可以发现抽象的、主观的塑造方法在魏小明雕塑中的重要地位,而这种抽象的美、极度主观化的形体,拉开了魏小明雕塑与追求客观再现的写实主义雕塑的距离。(图1) (图2)
值得注意的是,在魏小明塑造的众多充满英雄主义观感的身体里,却隐藏着一种悲剧性因素,这种悲怆感隐藏在诸如雕塑《河床》中男人躬屈的姿态里,也隐藏在诸如《角力》因对抗而极度扭曲的身体中——一种被压制的力量和不得释放的雄心,生成对抗命运不公的悲怆。与那些舒展着纤细手脚的女人体不同,这些如逐日的夸父一样的悲剧性形象,往往是雕塑家自我的想象和内心的投射,在向命运和社会的抗争中,展现了艺术家灵魂的孤寂和意志的坚韧。在解释他的作品《角力》时魏小明曾说道:“我也一直在寻找东西方文化的融合。比如这件作品是一头镂空的牛的形象和张力十足的男人体的组合,我想要给人一种精神上交织、挣扎甚至是互相牵制的感觉”。[]而另一件作品《逐日》则更为真实的表现了对命运的不屈和对梦想的追逐,雕塑中夸父所具有的那种坚韧的意志力、不言弃的决心,以及那种宁为光明而死的悲壮,散发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夸父是一个形体庞大的巨人,这个巨人不惧太阳毒辣的光射一路追逐直至身体龟裂、融化。所以我用一个强壮的男人体表现快融化的这个瞬间,是因为我能感受到夸父在融化瞬间的那种力量、不放弃的精神。”[]无论从何种角度,我们都能深切感受到一个用生命反抗命运、追逐梦想的英雄形象,而这个宁愿为亲近太阳而融化的英雄夸父,何尝不是艺术家在作品中塑造的另一个自己呢?(图3)
纵观中国现当代雕塑发展过程中对身体的表现,我们依然发现多数时候美的身体的缺失:虽然在20世纪前期中国现代雕塑发展之初,第一代留学西方的雕塑家如刘开渠、滑田友等创作了大量女人体雕塑,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宋明以来身体表现的禁忌,重新使“形躯之身”在艺术中彰显,但这种对人体的关注和表现,更多的成为西方客观理性的科学精神的象征,美不是最重要的,“真”才是人体雕塑的第一追求;新中国成立之初,在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影响下的“红色雕塑”,弱化了身体的性别特征,强调身体的阶级性、集体性,很少表现出身体的个体和肉身属性,身体成为了一种革命符号;虽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的开放,带来了艺术观念的开放,人体雕塑从禁忌中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之中,但在消费主义的冲击下,表现世俗、怪诞、欲望的身体形象替代了对美的身体形象的追求,甚至在观念艺术、装置艺术等新的观念冲击下,人体雕塑未等展现出新的面貌,便又成为保守主义的象征。在追赶一个个艺术潮流的过程中,艺术家为了证明自己艺术的先锋性或当代性,也惧怕于被快速行进的时代之车所抛弃,而辗转于无止境的对“新”的创新之中,艺术中被忽视的人体美,被电视广告中的性感模特所替代。恰恰是,以魏小明为代表的一些雕塑家创作的人体雕塑对“身体”这一主题的弘扬和坚守,不仅是中国现代雕塑身体表现缺失部分的弥补,也是中国自宋明理学及儒家伦理规训下“形躯之身”隐退后的一种回归。
如果对比中国近现代社会中个体的身体被挟裹在集体、国家和革命信仰之中而丧失独立价值这一事实,则更能明晰独立、自足、自在、美的身体之于中国社会的价值所在,正如20世纪80年代初在个人精神废墟上的中国,忽然传来邓丽君充满温度、自在、优美的歌声一样,在个体价值消隐不见的荒野上,魏小明那些美的有些极端的人体雕塑,也具备了冲击人们麻木神经和干涸情感的力量。
对人的肯定和颂扬,是魏小明人体雕塑的显著价值之一,而这种肯定与颂扬,正是通过“美”这一特质呈现出来的。维特根斯坦说 “人的身体是灵魂的最好图画”,是美好灵魂理想化的外在显现。人对身体之美的追求,是伴随着人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和个体的解放而产生的,或者说,对美的追求和表现,是实现了“人”精神独立的同时最自然而真实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魏小明人体雕塑呈现出来的美,正是那些“解放了的个体”和拥有“独立而美好灵魂的人”所能呈现的,这种建立在个体价值之上的“美”,因超越了对美的观看,而具备了深厚的人文价值。
真实、纯粹和美,其实都是人性被解放后的本能需求,因为探求真实,让人认知自我;追求纯粹和美,让人生饱含诗意。对人体之美的赞美,实质就是人的赞歌,“美”通过雕塑得以永恒,是雕塑家为“万物之灵”的人,所雕塑的永恒纪念碑。(图4)(图5)
二、诗意空间的再造
除却美这一显著特征外,魏小明雕塑的第二个特征是作品中诗意空间的营造。与部分追求客观真实的现实主义雕塑家群体不同,魏小明雕塑所呈现出的气质“浸润着某种源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精神意味”[],充溢着诗意的表达。所谓诗意,我们通常理解为诗歌意象及其传递出的美妙意境,而意象是 “诗人主观印象感觉亦即主观情思对客观具象的能动的胶合”,[]意和象的互动交融,让我们能够体会到一种多义的、朦胧的、未定性的、富有想象空间的意境之美,我们姑且把这种意境之美称之为诗意。对于诗意空间的营造,文字具有天然的优势,因为文字本身具有着多义性和抽象性,容易在词句的组合变化中,留置出语义的模糊地带,为主观情思和想象的介入提供广阔空间。而雕塑则是坚实之物,确定的形体和能够触摸的真实空间,让雕塑艺术不容易像文学作品那样,呈现出诗意美感,而魏小明雕塑作品中对诗意空间的营造,正是通过对客观“物象”的主观再造,以减少主题、内容、形体的确定性,增加雕塑的多义性和抽象性的方式来实现的。在这一实现途径中,我们就物象、意象、意境三者的相互构成关系,来进一步分析这种诗意空间的生成。
首先,就雕塑艺术而言,物象是指客观的物质对象,是构成雕塑的物理空间和物质实体;意象指创作者的主观意志和情思,当这种意志或情思转换为艺术创作的时候,首先会在艺术家脑中形成一个想象中的、朦胧的韵律或形象,也就是郑板桥所谓的“胸中之竹”,艺术家依照这个模糊的意象制作一个真实物体的过程,就是雕塑创作。由此可见,雕塑中诗意的产生,首先来自艺术家对形而上、超越世俗、热烈而纯粹的精神追求和情感投入;其次,来自艺术家在雕刻或塑造时为呈现心中意象对形体造型的主观处理。不难发现,魏小明雕塑中所呈现的诗意美感,一方面源自他对美、温情、爱、力量、崇高等形而上精神的追寻,另一方面则来自他为呈现这种精神追求所塑造的极端纤细舒展的女人体和浑厚如山壑的男人体。
魏小明对雕塑形体极度主观化、个人化的处理,正是藉于对故事、内容、主题、个体形象的剔除和对精神的提纯,就像诗意产生于诗歌语言的纯粹一样,魏小明雕塑的诗意也同样产生于艺术语言和精神的纯化。翁剑青教授在文章中表达了对这种主观化处理的理解:“在魏小明的雕塑中,人体的比例大多被拉长,在细节的处理上予以了理想化及类型化的处理,如四肢和手指、脚趾及脖颈等部位的夸张、概括与修饰,欲展现出作者对女性、人体、爱情和生命之诗意的理解和表现,以突出人性中崇高、美丽和诗性的一面,同时也一再流露出生命中恬淡的惆怅与肉身的纤弱”[]。在魏小明雕塑作品《心舞》中,翁剑青教授所描述的作品特征表露无遗:拉长的人体比例、理想化的身体特征,夸张的手指、修饰的脖颈,崇高、美丽、诗性、惆怅、纤弱。魏小明通过心中对人体的想象,“再造”了一个符合其精神需求的新形象,因为魏小明作品表现的实质不是人体,而是精神和情感,人体只是形象化了的精神,一个精致而完美的情感的容器。《心舞》中经由艺术家想象创造出来的女孩,呈现出明显的纤细、纯洁、诗意的特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被极端拉长的身体比例,这种比例的拉长不是平均的,而是一种在合乎美的原则下的拉长。人物姿态上,女孩高跷右腿,舒展手臂,颔首闭目,似乎沉浸在自我的小小世界里,而纤细到极端的身体,似乎剔除了女人肉欲的象征物,唯剩精神的美感。在现实中,没有一个真实的模特儿能拥有如此丰满的特征,或许她是美丽的,但不崇高;是崇高的,但不诗意;又或者她是诗意的,又不超然,因此艺术家只能通过想象,再造一个完美的“人”和这个“人”的完美身体。(图5)
再者,意象与意境,虽皆着重于“意”,有其相似之处,但也有明显的不同:意象有其形象性,能够通过物象来表现,而意境常常是一种感受,一种空间的气质。也可以理解为:“主观与客观、印象的虚与物象的实的交融,造成意象自身的张力,形成空白点与意义的未定性,激发读者运用所感所思以及个体经验加以解读。这样的‘妙’境常常得益于意象营构中实写与虚写交叉互补的行文方式:‘实以带虚,虚以衬实,实者形神毕现,虚者灵气所隐,实起虚结,虚起实结,虚虚实实,相映成趣’[]”。[]
魏小明雕塑呈现出的意境,实则是一种中国山水画中时常出现的世外之境,一种超越了现世的理想之境。同时,去除了人体雕塑的世俗性,使得这些优美的“女人”像来自世外的桃源,更有一种东方“仙子”的纯净和浪漫,这种超然物外的诗意和东方气质,也许正是外国观众看到魏小明雕塑时所感叹的“东方美”的缘由。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一文中,诗人对生活在桃源之中的人的描述是“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种怡然自乐,不知魏晋的超然、自足精神,在魏小明雕塑中多有体现,诸如《伊人》系列的春、夏、秋三件作品、爱情主题的《永恒的瞬间》《探戈》《生命的溪流》,以及《妞》《彩虹》《温泉》系列作品,人物都有一种置身世外,怡然自乐的单纯和浪漫。但桃花源的超然,还是有凡俗的成分,在魏小明另外一些雕塑《风花》《天使》《风》《河仙》《爱心女神》等作品中,则全然超越了世俗的情感,塑造了一众“东方仙子”形象。这种东方意象的继承,魏小明是无意为之的,或许在他大学期间行走于黄河两岸体验生活的时候,中国的传统精神就已经深入到他的血液中去了,而他在青年时期生活的困顿中、命运的崎岖中所追寻的,不正是艺术中的那片桃花源吗?尽管他有些作品名字称作“天使”或“女神”,但那种充满生命超越感的浪漫和诗意,显然不是来自身心二分的西方,而是具有整体生命观的东方。
(图7)
三、承接两个传统的浪漫幻想
魏小明早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接受过系统而全面的中国艺术教育,其后进入奥地利维也纳美术学院留学,又沉浸在西方艺术的温泉里,从两个艺术体系和传统中汲取营养,并形成独特的个人艺术语言。如果说美和诗意是魏小明雕塑在形式和气质上的两个明显特征,那么从表现主题来看,浪漫幻想则是他雕塑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第三个特征。
需要明晰的是,何为幻想?
康德曾把想象力分为“再生的想象力”(Reproduktive Einbildungskraft)和“创造的想象力”(Produktive Einbildungskraft),其中第一种想象力是指回忆或联想的能力,第二种想象力是指能够重新整合、建构客观现实之外事物的能力,显然幻想就属于康德所说的第二种想象力,是特殊形式的创造性想象。在哲学家张世英看来,“想象”最经典的定义是“使本身不出场的东西出场”的“能力”或“经验”,是“飞离在场”[]。显然,如果以“飞离在场”来审视魏小明的人体雕塑,至少可以发现两个方面在想象上的创造性:一是魏小明雕塑中的人物不是现实中人物的刻画和再现,他们都来自现实之外的完美想象,是艺术家幻想出来的完美的人。这显然与现实主义作品中那些有着明确身份和个体形象的雕塑人物不同,魏小明雕塑中的人都是凝练了某种美的特征的一类人的表征,与现实中的个体并无直接对应关系,正如他作品名称如《河仙》《天使》《爱心女神》《三仙女》《风》所表露的,他们都是飞离现实之外的幻想之物,甚至是带有神性的神话人物。另一个方面是魏小明雕塑中基于想象而塑造的人体造型,女人们极端修长纤美的形体和男人们“自由生长”的肌肉,同样无法在现实中人的身体上找到对应,它们是幻想出来的人和幻想出来的身体,是艺术家再造的理想世界。
面对魏小明的雕塑作品,这些因幻想创造出来的人体因为其抽象的形式美、纯粹的诗意精神和浪漫的幻想,让观众在自由的想象中拥有了更大的审美体验。因为一般想象都有飞离在场的特点,而幻想则比一般想象具有更大程度的飞离在场的特点;人在一般的审美想象中可以因意识到飞离在场的自由而感到愉悦,感到一种美的享受,而在幻想中则由于这种更大程度的自由意识而感到更大的愉悦、更多美的享受[]。浪漫幻想作为魏小明雕塑的一个显著特征,与他在求学和创作过程中承接的中西方艺术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中国艺术思想和传统,是以形成于先秦(一般指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为两大根基的,秦汉以来的艺术也大多在儒道两种美学思想的影响下各自发展,或相互吸收补充。总的来说,儒家与道家,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儒家)强调的是官能、情感的正常满足和抒发,是艺术为社会政治服务的实用功利;一个(道家)强调的是人与外界对象的超功利的无为关系亦即审美关系,是内在的、精神的、实质的美[]。其中道家思想影响下最为重要的艺术传统,就是庄子开创的“……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庄子·逍遥游》)般充满着奇异幻想和浪漫主义色彩的艺术道路,这种全然不同于儒家理性精神和实用功利的艺术理想,在楚汉之际化作屈原《离骚》中美人香草、百亩芝兰、芳泽衣裳的艳丽想象和缤纷世界,继而成为南中国五色斑斓的艺术中的浪漫幻想传统。
偏居中国南隅的北海市,不仅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更在几千年前就已成为汉代的文化重镇之一,从北海已发掘的数以千计的汉代古墓,就能印证汉文化在古北海的繁荣。文化从来都有其强烈的延续性和浸染性,那些博物馆中造型奇异的铜马、铜牛和铜凤灯,以及遍布北海的汉文化遗留,使生长于广西北海的魏小明,不可能不受到强烈的楚汉文化遗产的影响。这种影响或是一种感性的、朦胧的对某种自由艺术的接受,或是一种对远溯至楚汉艺术浪漫幻想传统的承接。
当然,汉文化的浪漫幻想基因作为一种模糊的、不那么显著的影响力,未必直接导致了魏小明后来的艺术选择,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潜在的影响为魏小明未来的艺术道路铺下了一层底色,因为在他从大学毕业不久创作的连环画《黑骏马》和《一个女人的刚毅》中,就已完全显露出这种文化基因的端倪——据艺术家自述,当年为绘制《黑骏马》去呼伦贝尔大草原采风,拍摄了大量的照片作为素材,但由于胶卷意外曝光,致使没有一张照片留下来,后来的《黑骏马》完全是凭借印象和想象画出来的,不止如此,这部连环画的风格也不是那种写实的再现,而是一种对生活充满想象、浪漫的描绘。
魏小明艺术中的第二个传统,来自于他六年的维也纳美术学院留学生涯,其间尚盛行于维也纳艺术界的维也纳幻想现实主义学派,直接启发和促使了魏小明艺术面貌的形成,他在维也纳美术学院学习期间创作的系列版画《荒原之梦》,就已经奠定了其浪漫幻想的风格。维也纳幻想现实主义学派是20世纪40年代诞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意图改变当时奥地利保守文化倾向的艺术流派,二战后由于奥地利文化的保守主义影响,当欧美艺术家在摸索现代主义向后现代的转型之路时,奥地利的文艺界还处在古典主义的田园牧歌趣味与巴洛克艺术的繁复精致之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维也纳幻想现实主义学派诞生了。维也纳幻想现实主义的首要特征是强调幻想,这种幻想最初来源于超现实主义对梦境无意识的描绘和对理性秩序的反抗;第二个特征是强烈的宗教神秘主义倾向,宗教和神话,也是幻想现实主义画家们热衷的题材;第三个特征是对民族身份的挖掘和强调[]。当魏小明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维也纳美术学院学习的时候,正逢一些幻想现实主义学派的画家如豪斯纳、布劳尔进入美术学院任教,魏小明或直接受教于这些艺术家,或间接受到其他幻想现实主义学派艺术家如恩斯特·福克斯的影响,逐渐在作品中表现出强调幻想、使用神话题材创作的倾向,他在此期间创作的大量铜版画和木刻版画就表现出强烈的幻想特征。(图8)(图9)
或许可以说,魏小明承接的楚汉浪漫主义和维也纳幻想现实主义两个传统,在不同维度上促成了魏小明艺术风格的成熟,正是汉文化的潜移默化让魏小明在吸收维也纳幻想现实主义养分的时候,自觉剔除了宗教神秘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影响,走向了纯粹而浪漫的艺术幻想,而维也纳幻想现实主义学派之于魏小明的意义,是让他自然而笃定的找寻到了属于自己的、早已流淌在血液里的艺术理想。
结语
2016年建成于长春世界雕塑公园的魏小明艺术博物馆,共收藏了魏小明迄今为止创作的近300件雕塑和160余件绘画作品。无一例外,这些作品全部以人体为表现对象,艺术家对人体的关注和兴趣,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艺术主题,把它们视为人的普遍情感、恒久精神和完美性的最佳载体,并以此表现出人所拥有的智慧、尊严、美感与生命力。从这一点来说,魏小明的人体雕塑作品,与20世纪初经由第一代雕塑家引入中国的人体雕塑有着很大不同,也与后来承接苏联现实主义传统的人体雕塑有着很大不同,这其中最大的差异就是:魏小明通过对想象中的完美人体的表现,肯定的是人的价值,人的解放,是对生命之美的赞歌。这种对人的肯定与歌颂,只有放置到中国雕塑的“身体”表现的历史中,才能彰显其工作的意义。
在个体被消费主义挟裹的今天,人的精神仍旧充满异化和虚无,远离了生命自身的和谐性,更勿论诗意和崇高。作为那些意识到自身价值和精神解放的个体来说,我们应该如何关怀自我? 魏小明作品中表现出的唯美、诗意与浪漫幻想,包含着生命的激情和本色,它们,预示了一个美与超然的理想世界。
(本文发表于《美术学报》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