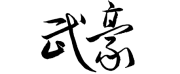每当斜倚在工作室的沙发上,目光在大大小小的作品间游移,便总会有一种奇特的熟识感,这感觉像回到故乡,有一群儿时的伙伴围簇在你的身边,让你感觉单纯而真实。如果说艺术来源于生活,那么很多时候,一个人的情感与性格,却是他童年生活的投射,尽管这种投射,时常被成年生活的表象所遮掩,或者在无暇的忙碌中难再追觅,但它是一条人生隐秘的线索,不经意间就会悄然显露。对于我而言,出现在我雕塑台上的山水虫鱼、飞云走兽,与那一个个自在自得的男孩儿,就是曾经那个年少的我,奔跑在山间林地、横躺在芳草原野上时每一个奇异幻想的重演,那个在繁华都市中羞涩、笨拙的我,却能够在自然中间,在原野之上,轻易寻觅到生命的喜悦。
山
中国人对山的情感,从几千年来的山水画传统就可见一斑。山不仅仅是风景中的山,也不仅仅是绘画中的形象,更是精神的寄托。它雄伟、浑厚,也宁静、灵逸,亦有简单和质朴,世界多变,人生无常,而山却横亘千古,静默无言。与西方艺术中对山川美景的描绘不同,我们从对山的想象中得到力量,得到慰籍,也得到生活的灵感与智慧,山并不是自然中纯粹的山,山是人的写照,是自我的投射。我作品中的山,毫无疑问来自我故乡那些低矮无奇树木甚少的秃山荒岭,它们不似范宽《溪山行旅图》中北方山峰的雄壮奇俊,也不似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中描画的南方山岭那般郁郁葱葱,充满灵秀,它们朴实无华,一如我的父辈们,但它(他)们给予我的,正是这份简单、平凡与从容,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我雕塑作品特有的质感。离开家乡生活在繁华京城的我,没法带走一草一木,却带走了家乡山的精神与品质。
如果说有另外一座虚拟的“山”总在我的作品中出现,那就是一种对规化生活的反抗——都市中的人对山的向往,对心灵得以舒展的静美境地的追寻。在我的系列作品《何处觅南山》中,就是这一精神意象的呈现。在《诗经·小雅·斯干》中有“秩秩斯干,幽幽南山”之句,就描绘了一幅涧水潺潺、清幽静美的南山景象,这件作品正是以南山之名,象征一种精神解脱后的平静之美。如作品名称所提示的那样,南山何处寻?这才是作品所要提出的疑问。骑飞马不可寻,驾神鹿也不可得,而那一只仙鹤,也带我们去不到理想的世界,南山其实不在海角,也不在天边,它就在我们的心里,马背、鹿背与鹤背上三个闭目自观的男孩,或许给了我们找寻答案的线索。
云
对云的幻想,多半来自它飘渺的诗意和随性无拘的形态。用雕塑来塑造飘渺无形的云,显然不如画笔那么灵动飘逸,但我依然需要一朵“笨拙”的云彩,来指向一处现实世界之外的纯洁、自由之地。因为有云的地方,或在山巅,或在天空,在我们肉体不能抵达的地方,自由的心灵却穿行无碍。如果说山的形象是一种恒静的美,那么云的意象,就是自由。自由对人的吸引,犹如蜜蜂翅膀下散发着幽香的花海,充满一种宿命般的致命诱惑。每个人都在毕生的奋斗中寻求自由。有人寻求财富的自由,以便可以拥有更多;或追求身体的自由,可以无所不往,享受感官的愉悦;或者权力的自由,掌控无数个匍匐于脚下的人的命运;但也有人,寻求心灵的自由与无碍,即使身陷庸碌的平凡之中,也能够在另一个飘渺之地,享受心灵飞骋的快感。云的虚无与飘渺,注定不能承载财富,不能安置肉身,更不可展示权力,但它可以于物质世界之外,向你预示一片洁净的天空。
出现在我雕塑中的云,同样来自这种自由的意象。我也通过这些漂浮在世界之上的云朵,来与世俗的现实世界划出界限,使雕塑作品营造出一种自由、诗意和浪漫的东方意境。正如作品《仙山雪莲》所呈现的那样,仙山、祥云、雪莲、可爱的小人儿,共同制造了一个我们期望的梦境:如仙山般清静明媚,如雪莲一样单纯无染,享受世俗之外的这份清静无羁,自在而逍遥。同样在《幽梦》两件作品中,一个脚踩云朵飘浮在梦境中的女孩,和一个倾斜身体似乎梦游仙境的男孩,塑造了与《仙山雪莲》相同的自由之境。当你忘却身体的欲求,它便不再成为自由的羁绊。
我想对云的热爱,对这种飘渺的心灵自由的追寻,正是东方人的智慧所在:我们心中明晰真实与虚无,从来不会陷入极端的追求之中,我们一边置身于红尘俗世之间,也一边仰望星辰,给心灵以自由。
人
世间最复杂的莫过于人,所以我喜欢的人,多半有趣而简单。他们洞悉生活的真相,不沉溺于人情世故的周旋,也不自设城府坠入荒谬的角逐,把人生变成一部复杂而无趣的戏剧。庄子在其名篇《逍遥游》中对于人精神的解放有过精辟的描述,那就是“逍遥”。所谓逍遥,就是只有做到“无己、无功、无名”的无所束缚才能达到真正的自由境界。对于生活在世俗世界中的我们而言,庄子的逍遥境界太过纯粹而显得遥远,但朝着他给我们描绘的美好理想,稍稍涤荡一下沉重的心,或许就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让你在忘我的追逐中,重新发现心灵的需求与喜悦。然而不幸的是,在我们这个纷繁烦扰的现实世界里,自我的膨胀、功利世俗的贪欲以及理想破灭下自我灵魂的沦丧,使得无所羁绊的自由与宁静依然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童话般的梦想——这便是我一系列雕塑作品创作的精神源泉与需求。作品中不断出现的仙山、祥云、异兽乃至沉溺于自我的可爱男孩,都是对单纯与自由的渴求。我想通过雕塑创造出一种理想的情境,来安放现实生活中我们无以寄托的的心灵。
我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大多垂目自得,沉浸在自己美好的个人世界,他们似乎脱离了现实世界的牵绊,或游嬉于山峰之上,或怀抱云朵,与禽鸟为伴,他们无所事事,像漂浮的云,随遇而安。《风》《溪》《谷》三件作品中的男孩,他们或像在聆听山风低吟,或像蹲坐溪边感受清水漫流,又像在山谷之中怡然自得,寻求着美妙的平衡,没有真正的风,也没有真正的水,但他们感受到的,一定不是杯盏交错的声音与喧闹。在《菩提树》与《须弥山》中,树与山的形象并无特别之处,它们平凡无奇,如野外常见的万千形象,正是这种平凡无奇,才提示我们菩提本无树,须弥亦无山,所有一切都是外相,真正让你得悟的,不是菩提树和须弥仙境,而是你的心灵。我去除了雕塑中人物的头发、衣物——因为无论发型、服饰都脱不开真实世界的影子,而我所塑造的,是一个单纯的梦,它们从庄子开始,就漂浮着,不曾逝去。
艺术来源于生活,但艺术不必一定表现生活,我们追逐的物质世界已然太多,所以梦与幻境,才弥足珍贵。一件作品从无到有,一点点在手中完成,犹如一个生命的诞生,在时间的累积中,逐渐变成它们自己的样子,而作品也使我想要构建的飘渺世界更加丰满,这是艺术家的辛劳和快乐所在,而我希望分享这份快乐。
对我而言,选择雕塑作为我创作的手段和艺术实现的方式,符合我对于真实、可感、单纯存在之物的眷爱,或者说,可被直接感知的形体之美和不可描述的情感力量,远胜逻辑而玄妙的文本解读,我希冀以一种更加本质的语言,单纯、直接、有力的表达情感,而非知识。我也希望以一个东方人的视角,呈现充满诗意、温情与浪漫的东方情怀,用作品给予现代文明困扰下焦虑的人们些许精神的慰藉,使观者在触及雕塑的同时能够进入作品背后的精神乐园,心灵在安静与放松中得到深层的愉悦体验,而非娱乐之后那种肤浅的快乐。
回归平静,也回归诗意的精神空间。